|
ck电影在线看最热影视 https://www.ck77888.com 24小时,或许是重复着昨日平淡的普通一天。 但有时,也可能是生命剧烈的转折点,是高度浓缩的跌宕,是回顾一生中无数个「一天」时,仍然会精准翻涌的记忆。 这些镌刻在记忆中久久不会褪色的「一天」,便是人们活过的印记。 这里是视觉志推出的全新栏目——《24小时的朋友》。 栏目将用纪实的手法拍摄普通人不普通的24小时,褪去时间、秩序、人际隔阂的外衣,真切地挖掘人生的赤裸和粗粝,寻找活着的真相和生命的力量。 我们记录的第一位朋友,是北漂5年的30岁单身女孩娜娜。 娜娜是河南周口人,出生在一个农村的五口之家,她是长姐,往下有两个弟弟,一个在杭州工作,一个正在念大三。 她的家庭不算富裕,但也不至于拮据。爸妈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她的所有想法,在婚恋上依然有较为传统的观念,但整体的家庭氛围仍然有朴素、温馨的爱和亲情。 在农村女孩中,娜娜一直觉得自己还算幸运,能顺利地读完高中,考上大学。 2016年,她从河南大学对外汉语专业毕业。考研失败后,来到北京发展,转眼就是5年。 在今年秋天正式来临前,她没有任何征兆地辞掉还算稳定的工作,退掉合租屋,买了一张回家的高铁票,正式结束北京的生活,就此开启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崭新旅途…… 刚开始我们都很奇怪: 娜娜在北京生活得好好的,为什么会走得这么突然? 而经过24小时的相处,我们在她身上,看到了「30岁女性面临的种种隐形压力」,和「部分小镇青年无可奈何的人生范式」—— 费尽力气逃向都市,最终却不得不回归故里。 以下是她的自述—— 离京的决心 7月中旬,我跟主编、周围的朋友提起离职回家的打算。 她们都觉得很突然,劝我别冲动、多想想,回家很难有这么多工作机会和相对自由的生活环境…… 这些现实方面的顾虑,我不是没有想过。北京的文化生活、发展空间、比老家开放许多的社交氛围,我也很不舍。 但大家看不见的,是我过去一段时间承受的负面情绪。 娜娜在办理离职手续 我在北京做过3份工作,最近这份是内容编辑,做得最久,整2年时间。 大概是年初春节返工之后,好长一段时间我的绩效都不是很好,看到同事都在拿奖金、晋升,只有自己还在原地踏步,心里就很焦虑。 那时受疫情影响,很多公司都在裁员。 之前工作认识的朋友说他们那边都裁掉一半了,我也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辞退。 越担忧越会陷入自我怀疑,更加写不出东西。 我不太习惯主动和别人诉说困惑,所以有时候会胡思乱想,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走这条路。 虽然很努力往前追赶,但总有人比自己进步得更快。 这种焦虑一旦有了苗头,就会像苔藓一样蔓延,也会渐渐麻痹对自我生活的知觉—— 老实讲,我已经想不起上次停下来给自己充电是什么时候了。 有时加班打车回家,会路过大厂的办公楼,即便是夜里23点,很多楼层依然灯火通明,人们就在格子间里埋头苦干…… 想到我也是其中一员,心情就变得很复杂,会觉得说「大家来北京都是讨生活,但讨着讨着就没有了生活」,这种状态真的是我想要的吗? 娜娜过去两年的工位 有不少当初一起来北京的朋友,因为类似的困惑,陆续离开了。 有的回家,有的是去南方城市发展。这一两年,他们的人生也稳步迈入新的阶段。 我家人肯定会着急,觉得「30岁了,在北京还没混出什么事业、对象也没处着,不如早点回家另谋生路」,逢年过节的相亲场合更是避免不了。 之前我都很努力去过滤掉这些声音,而且还有好闺蜜「相依为命」。 这五年我一直都跟她合租,平时会聊很多东西,可以说在北京,我有很大一部分情感寄托在闺蜜身上。 但7月底,房子到期,她打算搬去和男友同居,上班通勤也会更方便一点。我知道这很合情理,但心里还是有些失落。 感觉闺蜜的搬迁决定,是一根导火线。引爆了我之前积压的所有困惑、不安、踌躇和郁闷,也让我下定了离开北京的决心。 娜娜退租当天打包的行李 退租那天,我打包好大部分行李,准备寄回家里。 坐在堆满纸箱和编织口袋的出租房,那一刻我感到如释重负,终于结束了西西弗斯推动巨石般的日常。 从退租到正式离职之间,大约还有一周多的时间,我带着一些随身的行李,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70块一天的混租床位。 房子是三居室的公寓,每间卧室放了两张铁架床,租客流动性很大,我那几天的室友是一个早出晚归的姑娘。 想到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,也是在定福庄附近的两居和人拼床,只不过当时是和闺蜜,不是陌生人。 要离京那天的中午,我就坐在这个床位上收拾着最后的小物件。 忽然之间,这5年的生活碎片,像跑马灯一样从我眼前一一闪过,很难相信这都成为了过去。 但我也必须说服自己:这的确都成了过去。 留下来的野心 刚来北京的时候,我没有认真思考过离开这件事。 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法是「有过留下来的野心」。当时我给自己规划了一条人生路线,和现在的发展大相径庭。 我本科是河南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的,大学毕业后,一心想考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的研究生。虽然北语不是211、985高校,但的确是对外汉语的领头羊。 我想着顺利上岸的话,可以在就读期间出国交流、教学,积攒一些经验,毕业后能凭硕士学位和履历在大城市找到一份体面、工资高的教学工作。 但第一年,我没考上。 当时很不甘心,跑到北京投奔闺蜜,找了份工作在职复习,又考了一年。 还是没考上。 可能从那一刻起,我和北京的距离,就已经越来越远了。但当时的我依然不死心地思考「要怎么做才可以留在北京」? 娜娜很喜欢穿着汉服和朋友出去玩 最后想到两条路径,要么在国企或者体制内工作,要么赚的钱足够多,能在北京买上房。 买房这一点我挺早就放弃了,就是承认自己的普通吧,以我一己之力是达不到的。但进体制或许还有一丝渺茫的希望。 于是考研落榜之后,我又报考了两次北京的公务员,是军队里的文职岗。 当然……奇迹没有发生。 我身边也有在北京发展的朋友很积极地相亲,想通过结婚这条路径留下来,这无可厚非。 但我对情感生活的期待更倾向于找一个在北京共同发展、相互扶持的伴侣。 没有房子、户口也没关系,可以一起打拼。 之前在约会软件上认识过一些人,也和其中一位见过面。但对方想要快速发展到下一阶段,我又比较慢热,节奏不匹配就没有继续下去。 也有朋友介绍过同来北京发展的老乡和在老家工作的消防员。 老乡可能觉得我年纪比他大四岁,不太能接受,出来玩过一次后,就没有继续聊下去。 消防员本来聊得挺好,但始终觉得我在北京发展,短期更不会因为他回去,异地很难有结果,也掐灭了这段暧昧关系。 慢慢就会觉得,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真的很难。 娜娜和朋友吃完饯行饭在南门涮肉外 有时候,我会羡慕出生在一线城市优渥家庭里的孩子,譬如之前的一个同事。 她是北京本地人,独生女,家里条件挺不错的。出来工作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,挣的钱够自己花就行,朋友圈日常是吃喝玩乐,不会有太多生存危机和置业压力。 虽然我们之间的相处都是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个体去交流,但不得不承认,大家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、享受的资源,天差地别。 我记得很早之前,某个综艺节目做过一个实验。先让所有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,然后给条件筛选。 有些人的父母上过大学,往前走一步,没有的就留在原地。出过国的往前走一步,没出过的又留在原地,渐渐地,差距就越来越大。 我对这段的感触很深。出生带来的阶级差异,如今靠个人的努力真的很难去弥合。 同时我也羡慕,她不用为了追逐更优渥的资源、更好的发展机会,远离家人和常年的社交关系,始终能得到稳定而亲近的情感支撑。 不必像真正的异乡人一样漂泊,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寻找一丝确定。 或许这些支持,她并不一定真的需要,但却是我的「求之不得」。 回归故里 其实认真回想一下,过去的日子,我一直在试图往外走。 原因很简单,我相信外面的世界有更自由、光明的前景。就像海明威对巴黎的形容一样: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,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走到哪里,她都与你同在,因为巴黎是一座流动的盛宴。 大城市对我而言,就是那座「流动的盛宴」。 而家乡是「静止的湖面」。 娜娜2019年往返北京-河南的车票 我小学三年级之前,爸爸在当老师,他当时念到高中,回了村里的小学任教,我也在那念书。 三年级之后,小弟弟出生,爸妈为了多挣点钱,跟着包工头出去干房地产,我就开始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 初中到了镇上读书,我当时很想学一个乐器,但家里没有条件给我报兴趣班。小地方填鸭式的教育,也很难让人挤出时间去培养额外的兴趣。 甚至那时候,我都不知道少年宫是什么。 但大城市的孩子,去博物馆、艺术展都是家常便饭。 高中我考上市里的中学,在河南这个高考大省卷出一个不算太差的分数。当时我很想去外地,第一志愿想报考天津的大学。 家里人希望我保稳一点,让我填省内的河南大学,我还是乖乖听了话。 但专业上保留了一点小小的倔强,填了对外汉语,最大的动机就是可以出国交流教学。 现在分析那时想往外跑的心态,是有逃难的属性在的。 娜娜临走前在公司附近的混租房 家乡的人太多,发展太慢,视野太逼仄。而发展越慢,人才流失越严重,逐渐形成恶性循环。 我害怕留下来,这辈子的生活都会按部就班,精神也会被困在樊笼,停滞不前。 我只想往外走,怀着憧憬往更广阔的天地走,相信在那边一定有更为美满的生活。 但幸福真的可以越过阶级和出身的局限,降临在我头上吗? 我真的可以在享受自由的同时,抓住一条稳定的人生道路吗? 当时的我并不清楚。 直到5年后,职业的发展瓶颈、情感的漂泊无依让我难以喘息。我终于意识到,北京很自由,但我看不到可抵达的边际…… 「盛宴」背后的底色,是一片白茫茫的无依之地。 为了给当下飘摇的生活抓住一丝确定的东西,我选择回归故里。 至于为什么走得这么急,在离职第二天就马上回家,其实是我要赶去开封参加大学室友的婚礼。 娜娜参加大学室友婚礼 我们大学是4人寝,其他2个室友也都已经成家了。开封的室友结婚后,我就是全宿舍唯一的单身人士了。 婚礼结束后不久,我没有直接回老家,而是去了郑州——我大学期间的很多朋友都留在这里发展。 「报复性租房」似的,搬进了99平的两居室。房租一个月2500,这个价钱在北京的公司附近只能租下15平不到的小次卧。 但难过的是,我发现更大的房子、减半的消费、熟悉的街道、过去的挚友,并没有填补我内心的空缺,夜晚降临时,孤独感还是会从四面八方袭来。 我遁入了离京后的真空,不得不面临剧烈的疏离感。 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人生状态,也就是30岁单身、没房、没稳定的发展,是家乡同龄人中一个极为稀缺的样本,但在北京,和我类似状态的人太多了,没人会觉得,这有什么不对劲。 精神满足这方面,也空白了很多。 我无法再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地去剧场看演出,或者去国家博物馆闲逛一整个下午。 但庆幸的是,我终于开始静下来思考,自己内心缺失的究竟是什么? 娜娜在北京西站 5年前,我以为是那场「流动的盛宴」,却发现我像无脚鸟,疲惫地追逐着缥缈的美好。 离京时,我以为是「静止的湖面」,却发现在大海畅游后的自己,难以适应湖水的平淡。 后来我发现,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,看上去似乎是主动的选择,但实际上每一步,我都是以逃避的心态开启,被生活推着前进,成为了城市中一颗不值一提的螺丝钉。 或许我一直想要的,是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。 这种感觉如何建立? 多挣一点钱?确定一份可以长期干的事业? 我还没有很确切的答案。 前几天看朋友圈,前同事们一如既往地分享着生活的日常。不知不觉间,北京已经入秋。 这是我过去5年,最喜欢的时节。但点赞键按下之后,我知道: 北京那段生活已经彻底结束了,螺丝钉光荣退役。接下来,我要努力成为自己人生的核心。 娜娜的故事总是让我想起戴锦华教授的一段视频:《“逃”回小城市?一切就会好吗?》。 里面对于「逃离大城市」和「逃回大城市」的现象有鞭辟入里的讨论。 巨型城市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吸纳了大量的精英劳动力,但吸纳的同时也造成了浪费,导致精英劳动力过剩的现象,过剩之后要面临的便是再分配,通俗说法就是我们口中的「逃离大城市」。 这是一个必然的浪潮。 但巨型城市同时吸纳的还有文化资源,直到成为文化中心,这种中心状态自然也是一种文化垄断,加剧着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精神落差。 所以大城市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充满活力的社交环境,总是吸引着年轻一代,因为他们在精神方面有较强的需求。 而经历过大城市的繁华生活再回归的人,就会因为小城市的文化匮乏感到无所适从。 那么「怎样才是好的」,戴锦华老师给出的答案是—— 这个世界的选择并非二元对立,「倾听内心真实声音」,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,才是最重要的。 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么办? 法国知名社会学家迪迪埃·埃里蓬在《回归故里》中,或许给出了一种解法: 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什么,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。 现在的娜娜或许也不知道自己将变成什么,但她已经在改变自己这条路上行动了。 回去不久后,她以合伙人的身份跟老朋友开起一家儿童书店。店里会定期开展一些儿童教育相关的研学活动。 她知道从0开始创业,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,但自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即便失败了,至少也经历了一段不一样的旅途。 如果幸运的话,店铺的营业额能维持在一个不错且稳定的数值是最好的。 到那时,或许她会重拾当年未遂的心愿—— 再次考研。 希望我们都能听从内心的声音,成为人生的掌舵者。期待和你见证下一个不一样的「24小时」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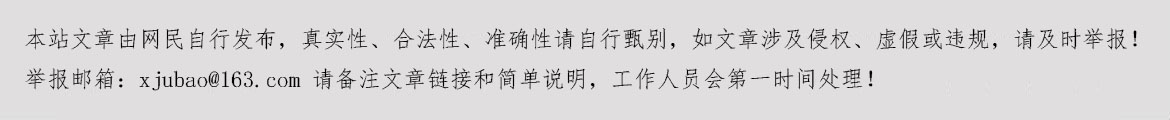
|